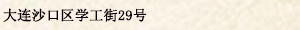渤大的树刘广远
刘广远
熟悉的地方无景色。
每天走过的小路,每天到达的地方,即使目见其亮丽或者繁华,然而,却极少被记录或者被叙述,有什么可说的呢?天天见,日日见,是啊,有什么可说的呢?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自然繁华着自然,人类忙碌着人类,即使美如画、美如歌,又如何呢?景色在远方而不在脚下。
然而,一天朋友的话却令我心中一动。他看了《渤大的湖》,张嘴调侃道:“朋友,你到过渤大吗?你看过渤大的湖吗?”我顿时哑然,因为,中学时,碧野先生的文章《天山景物记》,大家都记得顺口而有趣的第一句话——朋友,你到过天山吗?
朋友,你到过渤大吗?
这么风花雪月的句子,这么文艺十足的句子,竟然可以和一所大学联系到一起,妙不可言!武汉大学珞珈山的樱花、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、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……都曾经让我们流连忘返,然而,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,当你一转身,你会发现渤大的湖美不胜收,渤大的树壁立千仞。
一
渤大的湖是美丽的,渤大的花是妖娆的。
渤大的树是茂密的,渤大的冬是风姿的。
我们见过春的生机,夏的繁茂,秋的烂漫,然而冬的萧瑟,注意的人是不是少之又少?也许说这话,显得矫情,春意盎然,夏花美丽,当然草长莺飞,谁不生机勃发呢?冬天的日子,雪莱的句子大家都记得:冬天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是的,想到孕育春天的冬季,恰恰是该仰望和铭想的日子。
冬季,密密麻麻的树干,挤挤杂杂地枯草,一眼望去,也依然密不透风。每一株草,都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哨兵,等待吹起绽放的号角,每一棵树,都是一个孤独凛冽的战士,正在聆听天空的声音;——我最心悸的季节,也最默然的时候,是的,没错,一眼望去,密不透风,密密匝匝的树,白杨树、松柏树、紫荆树、槐树、柳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桑葚树、椿树、栾树、连翘、刺梅、木槿、紫荆、五角枫,大的、小的,长的、短的,葱茏的,稀疏的,散乱的,笔直的……风吹过去,竟然讶异地被密匝匝的树阻挡住前行的步伐,驻足在另一边的孩子可以听到风的吼声,然而帽檐只是轻轻地颤了颤。
冬季,银装素裹,白雪拂面。穿行在密而又实的树丛间,你清楚地看见年轮的影子。两个人才能搂抱的白杨,你可想见她参天的模样;瘦小的槐树,竟然一棵挨着一棵,顶住呼啸的北风,畅谈青葱的岁月,身边紧紧依偎的是小小绿绿的翠柏,也一棵挨着一棵,她们陪伴着光秃秃的小伙伴们一起成长,好似说:“奔跑吧,兄弟们,我在阳春三月等你们的新衣服啊!”《诗经?葛藟》里诉说:“绵绵葛藟,在河之浒。终远兄弟,谓他人父。谓他人父,亦莫我顾。”大地上的这些树木枝丫是不分离的兄弟。尤其是紫荆、连翘、榆叶梅、紫穗槐……她们的根深深地埋在地下,倾听着悄悄而来的柔柔的春风,倾听着潜伏的潺潺的水流,她们盘根错节、交缠拥抱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阳光透过密密的枝缠桠绕,形成碎碎的影,她们的茎部、枝桠是干涩而精干的,伸在凛冽的风中,恰恰是一种卓悦的姿势。
冬雪过后,大地肃穆,万物沉寂。枯草伏地,遍目苍黄,一棵棵仰望苍穹的白杨,围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场,而一块凛然的大象石默默的遥望,在一望无垠的细细的、挤挤的黄草中间,一棵并不高大的槐树,伸展枝丫、运如华盖,她的枝桠伸向遥远的遥远,好像询问春的讯息;伸向夜空的夜空,仿佛触摸到天际的星辰——一棵孤独的树,挺立在浩淼的草原上,既不高大,也不伟岸,然而环视周边,俯瞰众生,我存在我自由——我能想象她春夏时间的葱茏、绿叶满枝的苍茫——即使在苍苍的隆冬、在白白的大雪之上,她依然绽放出一种傲立的风姿、超拔的身影——
如果有来生,
要做一棵树,
站着永恒,
没有悲欢的姿势。
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
一半在风里飞扬。
一半洒落阴凉,
一半沐浴阳光,
非常沉默非常骄傲,
从不依靠从不寻找。
……
我仿佛看到三毛从沙漠走出,相伴着荷西,从落寞走向苍茫,从冬季走到春季。我甚至想,这棵树是不是根植于加那利群岛中的丹娜丽芙岛,哪里曾经属于两个人的天堂——她是一棵树,但站成了永恒。
渤大的冬是丰厚的,
渤大的春是简单的。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,“科普植物园”里的花啊、草啊,只要露出芽、探出头,就被早早地发现了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手指着黄灰土壤上的一抹草、一星花,“爷爷,绿——绿——花——花——”,老人正在端详一棵树枝上的花苞,快步走过来,抱起孩子,在尚未盛开的花树间,慢慢溜达。植物园的小广场上,晨光微曦,一位身穿白衣白袍的老者,一套太极下来,静处无声、动处有风,却气定神闲、安然若定,仿佛看见太极张三丰的飘飘的胡须,游龙般的身形,伴着身边高高密密的树木,简直进入深山老林,如果在看看,旁边小山上的仿古飞檐寺,奔流不息的小瀑布,清澈见底的小小的小河流淌,似乎是仙家圣地,然而,一位读书的女孩的身影,把目光拉回苍翠、流水、清净、宁谧的人间的早晨。孩子是纯净的白纸,新鲜的花草是动力,老人是沧桑的草纸,嫩绿的春是回味,他们都会在最早的时间发现,春来了!
年,朱自清写下了《春》,“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。园子里,田野里,瞧去,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。坐着,躺着,打两个滚,踢几脚球,赛几趟跑,捉几回迷藏。”他写完了,我们也背的烂熟,然后,我们在也不能好好地写春了。他写的时候,仿佛能看见他的笑脸,当时,朱自清刚刚结束欧洲漫游回国,与陈竹隐女士结婚,不久,喜得贵子,同时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,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,”自然这个时候,朱先生的文字美的不要不要的。
校园里的春,发现的早啊,一个又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,每天都要找一找,哪棵树又开花了?那朵花又含苞了?“风轻俏俏的,草软绵绵的。桃树,杏树,梨树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都开满了花赶趟儿。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。”校园里拍照的、录像的人就多起来了,三步一照像,五步一留影,老人、孩子也早晚都进来遛弯了,学生们在跑步、聊天,更有新婚的夫妇进来拍一张校园春花图——校园的春来得早些——所有的人都盼啊盼的,只要有一点点春的迹象,就被瞬间留影,就被图像记录,就被青春喊醒。一树花开,悄悄地开在教室的外面,一双善于寻找的眼睛就看见了;一叶草芽,默默地探出头来,一双每天都来这里散步的脚就停下了,蹲下身子,细细查看微暖的问候。渐渐的,人就多起来了,沿着湖跑的,围着树转的,闻着花香的,这个院子里,就是花的园,树的园,人的园,一幅繁闹,一幅灿烂。
二
春光的美是相似的,夏天则各有各的烂漫。
校园里的树,种类繁多,密密的,既有目见可识的,也有稍稍潜隐其名的,这些树形状各异,挤挤的,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粗的、细的、直的、歪的,她们都按自己的方式生长着,立在这里或附身而下,有的熟悉,有的陌生。
这个园里夏天是喧闹的、拥挤的。悸动的季节,丁香花开的脆生生地,满树满树的;连翘一小朵一小朵,密匝匝地挨着;桃花艳红艳红的,闪烁着人的眼……枝繁叶茂、繁华如翠的校园,我见过,去台湾国立大学游玩,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的母校的确名不虚传,高耸入云的椰林,遍地绿草如茵,棕榈树也入目皆是,然而是稀疏有度,显得空旷些。这所校园的密而又密的花林,残暴的簇拥着的烂漫张开臂膊喊:“我是北方的野花妹,我们是纯粹的美啊”,这种灿烂的花朵,爆炸般挤啊挤的,如刺开夜的繁星、如盛开空中的烟花,却不多见。法国画家让?安东尼?华托(JeanAntoineWatteau)有一幅《游园图》,似乎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场景,参天大树,花树覆盖,香气四溢,众人欢乐,只不过油画中的人吹的风笛,可能校园的孩子弹的是吉他。
丁香花开的时候,最好夜里。弥漫的花香让你的身心放松下来,轻轻向着空气中张开身体,就会被环绕,既不浓烈,也不刺人,是那种轻轻的、淡淡的、细细的点点微香,一阵阵随着微风拂过……唐磊有一首歌,就叫《丁香花》,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,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,多么忧郁的花……多么娇嫩的花,却躲不过风吹雨打,飘啊摇啊的一生……”,这首歌在网络流传于年,据说,是唐磊与一个绝症女孩曾梦捷相互爱恋的故事,为了完成女孩的临终遗愿,他写下这首凄婉动人的歌。的确,丁香花给艺术家的感觉就是遗憾的美好,让我们唏嘘不已,如果飘过淅淅沥沥的小雨,盛开的丁香,那意境就是让人无比的感慨与莫名的忧伤。宗璞写过一篇散文,就叫《丁香结》,“今年一次春雨,久立窗前,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。小小的花苞圆圆的,鼓鼓的,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。我才恍然,果然是丁香结!”但更被大家熟悉可能是戴望舒的《雨巷》:
撑着油纸伞,独自
彷徨在悠长,悠长
又寂寥的雨巷,
我希望逢着
一个丁香一样的
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她是有
丁香一样的颜色,
丁香一样的芬芳,
丁香一样的忧愁,
在雨中哀怨,
哀怨又彷徨
……
那是年,《雨巷》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第19卷第8号。戴望舒因宣传革命被反动者抓捕入狱,刚刚释放,面对着革命的低潮、未来的灰暗,他既有个人真实情感的失落,又有对政治理想空望的感慨。当然,李商隐的《代赠》这样描摹:“楼上黄昏欲望休,玉梯横绝月如钩。芭蕉不展丁香结,同向春风各自愁。”从此开始,甚至更早,这种愁绪已经与丁香有了联系,你看南唐李璟的《浣溪沙》:
手卷真珠上玉钩,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?思悠悠!
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三楚暮,接天流。
其中,无尽惆怅与丁香紧密相关。戴望舒大概从“同向春风各自愁”、“丁香空结雨中愁”的词句中触摸到同样的情境。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无论今人古人,都难亦做到,物语即人语,花语即人生。为什么是丁香呢?我觉得丁香细小而碎密,沁人心脾又绵远悠长,即可制高级香料,又可入百姓厅堂,美好的令人怜惜,芳香的令人驻足,然而,丁香终究会凋谢,丁香终究消散——丁香,丁香,“一个丁香一样的,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
而今,校园弥漫的隐隐的花香,又恰逢毕业季,孩子们一群一群四处照着像、留着影,这种淡淡的离愁别绪与满目盛开的风景天衣无缝地嫁接到一起——正好一对情侣走过,“你好,帮我们与丁香花合一张影,好吗?”我从恍惚中清醒,赶紧对好镜头,手指一扫,“OK,好了。”一张如花如美的两张笑脸定格在花间,只不过我有意无意的把丁香花与旁边的连翘花都拍进去了。看着他们远去的年轻的背影,听着他们的笑声,我心中默默地祝福——黄的连翘、紫的丁香还是蛮配的。
北门西侧有一个小园,自然而宁静,散乱而随意。
露天篮球场的东南侧,也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
这两个地方,休息的时候,我常常踱步过去。
相对于璀璨和绚烂,我更喜欢自然和宁静,哪怕是破败的宁静或者是杂乱的自然。因为自然里面孕育着最好的生机,最美的活力。
相对于干净、绚烂,我更喜欢杂乱的自然和随意的破败。喜欢恢弘的壮观、灿烂的绚丽是人之常情,驻足观赏那些无论人工或者自然而成的天然美丽与自然绚烂,一丁丁桃花耀眼枝头、一点点丁香入人心脾,谁能不被这样的一束挨着一束、一朵挨着一朵、一片挨着一片的满目风景逼闪着你的眼?谁能不被这无限的春色诱惑起无限的诗情?
然而,我更喜欢那杂乱的自然和随意的破败。那随风飘散的落花,无人欣赏、无人问津,然而却“幽径独徘徊”,而且“化作红泥更护花”,犹如夜的春雨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铺成一地,“冷落成尘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,你不会看到她的美丽,也无法体量她孤寂、落寞的心,然而,你去看看那树的茁壮的干——你去看看那翡翠的叶——你去看看那丰盈的果,你却只看到盛开背后的丰盈和铺满,没有看到落尽的花。
落英背后却留下无尽的苍凉与叹惋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里面有“黛玉葬花”:
(宝玉)便把那花兜了起来,登山渡水,过树穿花,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。将已到了花冢,犹未转过山坡,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,一行数落着,哭的好不伤感。宝玉心下想道:“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,受了委屈,跑到这个地方来哭。”一面想,一面煞住脚步,听她哭道是:
花谢花飞飞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
游丝软系飘春榭,落絮轻沾扑绣帘。
闺中女儿惜春暮,愁绪满怀无释处;
手把花锄出绣帘,忍踏落花来复去?
柳丝榆英自芳菲,不管桃飘与李飞;
桃李明年能再发,明年闺中知有谁?
三月香巢已垒成,梁间燕子太无情!
明年花发虽可啄,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。
……
黛玉葬花留下诗情一片,留下千古绝唱。虽然是想象的故事,却让人信之又信。唐朝,诗人刘希夷《代悲白头翁》中的“今年花落颜色改,明年花开复谁在”似乎是“黛玉葬花”的影子,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《楝亭诗钞》也钞录有葬花诗,一首是《题柳村墨杏花图》:“勾吴春色自藞苴,多少清霜点鬓华。省识女郎全疋袖,百年孤冢葬桃花。”追本溯源,“黛玉葬花”即是黛玉心情压抑、遇事不淑,作者自喻的情绪也是明显的。的确,繁华背后,一丛丛、一簇簇杂草、一片片、一叶叶松针,在盛开的春天、在满绿的夏天,显得那么荒凉与落寞,然而却又淡定而从容,犹如闹市中不合时宜的着装与扮相,犹如沙滩比基尼美女中的老僧——兀突而淡然,鲜明而迥立,既来之则安之,既在之则目之——今人不必忧古人。
我们的心境拟古而不仿古,能够看透衰败的背后历史的影像,黛玉葬的是情,我们寻的是理,即使风去沉枝、落叶,却能雕出宁静的心境。植物园有一口老井,估计是为了喷洒而凿的,上着锁,我估计一般人找不到;球场东侧是喧闹背后的寂静,也有一个盖子,底下是不是井呢?旁边有一个破败的机器房,这种在喧嚣的声音、青春的活力的背影下,却藏着这样“世外桃源”,也是非常有趣的,要是黛玉在这里葬花,我相信,不会有人看见。
春光有春光的灿烂、夏花有夏花的盛开,破败松枝与杂草却别样悠闲、气质深沉。破败处孕育繁华,寂静处潜有喧闹。破败的、腐烂的土壤却是最好的肥料,幽静、淡然的松柏是挺立的身姿。坐在松枝与杂草上,觉得厚厚的、温温的舒服,欣赏着人声鼎沸、青春物语中的小小的一点宁静、悄悄的一丝自然,天空的一片云彩慢悠悠地飘过,我常常在这宁静中体验生命的点滴流逝。在这里读书是非常好的,如果恰巧你读的是《呼兰河传》,你会看到哪里有着无数的动物、植物生长在童年里,“我家有一个大花园,这花园里蜂子,蝴蝶,蜻蜓,蚂蚱,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,黄蝴蝶。这种蝴蝶极小,不太好看。好看的是大红蝴蝶,满身带着金粉。”顺着隐秘的园子读下去,你会发现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都有着自己隐秘的小园,静谧而平淡的小园适合作家“寂然凝虑,思接千载;悄焉动容,视通万里”,可以有无穷的想象,这可能是大作家们的隐秘的、私人的灵魂通道吧。
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鸟语最是动人,两只喜鹊叫喳喳地飞走了,几只麻雀在天上旋过,一只吃饱的有着长尾巴的斑斓色彩的小鸟却停下步来,在厚厚的草地上蹦来蹦去,这般不知道名字的美丽的鸟也毫不避讳,也知道这地方人少物丰,动物出没,竟然也觉得这地方适合休闲?能在校园中,独见如此的浪漫与松弛,大概不是清晨,也应该是深夜,然而,午时的片刻淡定与寂静,真是极好的静坐、养生场所。
三
“科普植物园”里有花、有草、有树林,还有一个大棚。
年,正值三年困难时期。学校(渤海大学前身是锦州师范学院、辽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)贯彻“生活第一、健康第一、劳逸结合”的指示精神,在锦州西郊杨兴屯创建农场,大搞南泥湾运动,开始自种耕地。农场有土地25垧,除了1垧基建用地,其他17垧用于种植大田,7垧用于田园。我记得,当年上学的时候,期盼着劳动周,劳动周不需要上课,虽然劳动,但是大家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呼喊着、欢笑着,干点农活,挖菜地、捆谷子,割高粱、摘黄豆,那真是一派繁忙的劳动场景。
学生都是青春少年,还有的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”,正好区分一下什么是谷子,什么是小麦,怎么收割高粱,怎么扒苞米。中国大学生参与农业耕种历史,早已有之,年,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后,就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。由于绥德、米脂一带人口比较稠密,抗大就本着不与民争利的方针,一是把学员拉到偏远的山沟开荒种地;二是打“麻雀战”,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零星土地,大的几方丈,小的几方尺,三棵白菜,两棵南瓜,见缝插针。毛泽东也称赞说:目前讲起来,延安生产运动,第一是抗大。后来,文革时期,轰轰烈烈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,把所有的大学生都送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可就有点不太好玩,邓小平在年曾说:“国家花了三百个亿,买了三个不满意。知青不满意,家长不满意,农民也不满意。”后来,国家叫停了这种做法。
现在回看历史,唏嘘不已。时过境迁,对于如今的孩子,多认识各种植物、多熟悉各种蔬菜肯定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。
如今,“科普植物园”受人欢迎,我更喜欢到人少罕至的菜地、大棚走走。寂静无声的菜地、闷热潮湿的大棚,于观赏者来说,都不是最佳的胜景,甚至等而次之也谈不到,更多的是人迹罕至,或者寥寥无几。到这里干什么呢?赏花花香不热烈,赏景都是残枝烂叶匍匐于地,即使是生机的菜地,也是平常罢了,家常的小葱、平素的菜花,至于大棚,就是排满的尚未完全绽放的花花草草。然而,却有着一种不可知的魔力。
我常常凝望菜地、凝望菜地劳作的工人,偶尔非常想去大棚看看。一次,怀着惴惴不安的心,在大棚边上转悠,大棚墙上写着“花窖重地,公司承包,免开尊口,谢绝参观”,我小心的看了看,还是绕到另一个不是“重地”的大棚吧。
另一个大棚是敞开式的,我从一个没有人值守的口走进去,看见另一边20、30米处有两位师傅。我径直他们走去,工人师傅似乎没有看见我,丝毫不为所动,只是用余光扫了扫,继续干自己的活话,没活找活,一边和大爷一起,往小塑料筐里装细土、栽花芽,一边说:“大爷,挺热啊。”大爷说:“这个时候,都太阳快落山了,中午才热呢,但是花花草草都需要这个温度啊。”大爷非。一位50多岁,称呼为兄,更为合适,一位60岁有余,称呼为大爷,更为恰当。我蹲下来,没话找常和善,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和讨厌我,和蔼给我一一指点,对红、芍药、菊花,等等,而且大爷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花的知识。浇水不能浇太多,干透了就浇,但不能总浇,不能总透着湿气,太多的水也会破坏植被的根系;不能浓妆艳抹地在大棚里转,会挥发和刺激花的成长。虽然我是在帮助他们劳动,可是我的劳作很显然就是形式,而且一点也不如人家做的专业,即使是栽种小小的花草,可是有的需要手指摁压,我却不够用力或者摁压位置不对,师傅还得把我的小菜筐拿过去,再进行重新的整理。蓦地想起毛泽东当年的话语——向劳动人民学习。
他们没有呵斥闯入的陌生人,不但没“驱逐出境”,而且欣然而温暖地接纳了我,悉心与我交流,并告诉我如何养花、种草,自然地善意、自然地热情、自然地朴素、自然地豁达,他们的身影就是我的父辈,是养我、育我、教我、省我的先生。《诗经?伐檀》: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猗。不稼不穑,胡取禾三百廛兮?”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中,诉说一个拉车工人的善良,然后榨出自我的“小”。其实,不必拔高地对师傅们进行赞颂,也不必在面对粗野的时候去斥责他们,我们每天都在欣赏这些植物,却也应该知道背后的耕耘者。我好奇,他们是如何每天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?对于劳动的师傅和他们的管理者都是不小的挑战。我没有发现管理者的身影,我唐突地问了:
“师傅,怎么样计算工作量呢?”
“按天计,总量在哪呢,每天都挺忙的。”
“师傅,那这个菜,最后是大家吃了还是拿家去?”
“菜,学校说,主要是孩子看的,长出来,可能就有的老师要,有的大家吃了。”
菜园里,各种植物正蓄势待发,暗暗伏力,称谓“百菜园”。我看了看,有我们熟悉的高粱、黄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苦苣、油麦菜、辣椒、萝卜、茼蒿、韭菜、空心菜、毛豆、豇豆、生菜、茄子、向日葵、绿豆、菜心、荞麦等,也有我们略感陌生的菜豆、曲麻菜、苦麻菜、补肾菜、莴笋、番茄、飞碟瓜、臭菜、油菜、芝麻、苏子等,而且这些,每个小菜地都有牌子,我都记下名字、拍了一下,珍藏起来,留待学习,毕竟书本上的样子不如实际长出来的真实啊。还有一种菜就有数个品种,比如番茄,就有黄圣女、大黄、红圣女、红珍珠、绿樱桃、贼不偷等,哈哈,看来黄圣女、红圣女、红珍珠、绿樱桃等都按名索骥,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、什么品种,至于贼不偷,我都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西红柿。仲夏就要到了,那个时候,红的辣椒、绿的黄瓜、紫的萝卜,高大的高粱、丰满的谷子、矮壮的黄豆,有棱有角的补肾菜、形状各异的飞碟瓜、苍翠蓬勃的苏子叶,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到五颜六色、丰富灿烂。
我期待着这些农业作物长出来的时候,带着学生们来辨别——这种现实的心灵鸡汤应该胜于千百次说教。
你吃的每一种粮食,是什么样的?
你吃的每一种蔬菜,是怎么来的?
实物的认知、现场的学习,我想这和书本知识一样重要。
夕阳的光洒下来,从枝繁叶茂的树林的缝隙中,洒到大地上,不是色彩斑斓、花枝招展,土黄色的温馨、淡紫色的素淡、墨绿色的活泼,却是无限纯净、充满生机。
作者简介
刘广远,男,吉林大学博士,渤海大学教授,渤海大学社科联秘书长。辽宁省高校首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,社会兼职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,辽宁省美学学会理事,锦州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。
渤大新媒体工作室出品│如您喜欢请点赞转发
如想投稿,请联系后台
更多资讯,还可点击查看历史消息
----------------
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