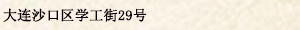作家地理生活在别处贝鲁特手记陈平1
贝鲁特手记
陈平
贝鲁特市区
1为什么贝鲁特?
乍到贝鲁特,四处寻寻觅觅,终于游荡到市中心的星形广场。
广场中央一座钟楼,呈五角星状放射出五条步行街。街上餐馆林立,各在道旁撑起红绿阳伞,别致的餐桌椅连绵排开去。在无序的车阵和街道迷宫中巡梭已久,这份亮丽和安逸让我顿时放松,感到既饿且累,于是拉开把椅子,向菜单上胡乱指点了一份食物来充饥。
侍者上菜,居然琳琅满桌:瓷碗里是用蒜和橄榄油调了味的稠厚酸奶油,洁白里带点森森绿意。竹篮内盛面饼,贴在炉上烤到两层面皮间热空气膨胀,鼓起如胖小孩的两腮。《出埃及记》里上帝晓谕摩西:“使亚伦及其子成圣为我祭司,祭品取一公牛犊,二无瑕疵绵羊,细麦粉做成无酵饼和调油无酵饼和抹油无酵饼,盛放篮里和公牛绵羊同带来。”①
眼前的面食,该就是这种古老更甚于《圣经》的无酵饼吧?一腌渍小碟,腌橄榄渍茄子酸黄瓜番茄干。一生菜巨盘,大朵甜椒番茄,迷你红萝卜胡萝卜和樱桃番茄,簇拥着水嫩一棵莴苣菜心。
这小碟巨盘,侍者殷勤说,是奉送的。
撕开面饼,抹上酸奶,随意夹进一叶莴苣、两片番茄、一点酸黄瓜,咬一口,舌上同时有了酸奶的肥腴芬芳、生菜的脆嫩清甜、面饼的嚼劲和谷物烘烤的香味。再拈个腌橄榄,添一丝悠悠不尽的咸鲜。
黎巴嫩菜系含大量新鲜蔬果,烹饪独到,在中东欧洲享有盛名。在黎巴嫩进餐的体验是地道东方式的:佳肴满桌的丰盛,众人分享的平等。最亲切的是那份东方式的随心惬意:可使刀叉可用手、随意往面饼里夹各色菜肴,品品这个尝点那个,间中不妨高谈阔论手舞足蹈,再悠悠然抽上一壶阿拉伯水烟。虽然当地人崇尚法国文化,但正襟危坐的餐桌礼仪就让高档法国餐馆独享吧!黎巴嫩餐桌上,套一句老子的话,是大礼无仪。如果从饭桌上可以认识一个国家,黎巴嫩是何等滋润丰饶,她的人民何等懂得享受生活。
然而这个懂得享受的国家,上世纪打了场历时十六年的内战。以贝鲁特为主要舞台上演的一幕幕劫持暗杀的血腥活剧,通过各大媒体传遍世界深入人心,乃至于内战平息十三年后,朋友们仍如此发问:“为什么要去那种危险地方?”
也许是这片土地太神奇,让人无法抗拒?
《圣经》里喋喋赞美过黎巴嫩的雪松泉涧。据统计,《圣经》里前后七十五次以赞美的口气提到黎巴嫩山的雪松泉涧。阿拉伯的沙漠和稀树草原浩瀚无垠,边陲上竟有如此一带好山好水:雪峰晶莹,植被丰茂,清泉百重。前有蓝如梦幻的地中海,后有莽莽苍苍的荒漠景观,映照之下美得触目惊心!归来后检索旅行印象,想到李白《菩萨蛮》词有句:“平林漠漠烟如织,寒山一带伤心碧”,这构词奇异的“伤心碧”三字,借来形容黎巴嫩很传神。
贝鲁特,神奇土地上的迷人之城,它两面临海,徜徉城中,抬头不经意间就看到了地中海那抹蔚蓝色。钢筋水泥的丛林、浊乱不堪的车流,给这蓝色一衬,再丑陋者也点铁成金,堪入名画。人若身处城中最杂乱的环境,加上六月日头晒得身心俱疲,只要瞥见这抹蓝色,顿时也便神清气爽心静如水了。
蓝色之城贝鲁特,由青铜时代来到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建立。贝鲁特其名,一说得自城中鲜活的井泉,一说是城中首位王后之名。现代贝鲁特的首度繁荣在十九世纪。工业革命后西欧富裕,对奢侈品胃口大增,黎巴嫩的蚕丝贸易应运而生,山中农田曾半为桑,至今仍可见保存完好的丝厂和仓库。贝鲁特港里,蒸汽船满载蚕丝驶向法国的里昂和马赛;致富的丝农们亦合家乘船游历法国。
蚕丝贸易使贝鲁特成为发达的港口城市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贝鲁特更提升为中东的金融中心。当年设在贝鲁特的银行,据说比伦敦的更多。
它也是中东的旅游中心。黎巴嫩与法国渊源甚深:十六世纪,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结盟对抗神圣罗马帝国,将地中海东岸单开放给法国进行贸易,并授权法国国王保护当地基督徒;一战后这一带又成法国托管地。因此贝鲁特街头往往可见巴黎式小景,法语也比英语更为流行。旅游季节,沙漠阿拉伯人蜂拥而至,享受它的宜人天气新鲜蔬果,和法国之外的法国风情。欧美旅游者亦欣然前来,领略中东情调。贝鲁特更为人们提供放浪夜生活和洗钱的方便,宛然中东地区一枝“恶之花”。
内战一度毁了这个享乐者的天堂,却为它带来别一种怪异魅力。局部断续的战争,其血腥悖理与日常生活的温馨正常紧紧纠缠,造成荒谬感和黑色幽默感。如下一类轶闻广泛流传:东西贝鲁特流血交战之时,大酒店仍不屈不挠坚持五星级服务水准。战前酒店接待员问订房者:“先生要看街景还是看海景的房间?”战时他们问:“请问要狙击手那边,还是汽车炸弹那边房间?”一样贴心的服务,只是些微细节不同。酒吧生意也依然红火,一只五彩鹦鹉,营造出异国情调度假气氛。能言鸟开口时,学舌的却是三不五时炮弹呼啸而过的尖利哨音,令酒客们竦然酒醒。如此内战轶闻俯拾皆是,叫听者骇笑不已。虽然和平恢复已久,它们为贝鲁特涂抹的传奇色彩并不见黯淡。
传奇城市贝鲁特,迷人惑人也发人深省。曾任《纽约时报》驻贝鲁特战地记者的弗来德曼写道:“贝鲁特决不只是一个城市,它是一个理念——一个不只对贝鲁特,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意味深长的理念。”托玛斯·弗来德曼,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,纽约,法拉·斯特劳斯·吉罗克斯出版社年版。我在飞贝鲁特的航班上断断续续读他的书,读至此飞机降落贝鲁特国际机场,正好一探究竟,这座城市代表什么理念?
游后回顾,感受深切:造访贝鲁特,有太多的理由。
2西区故事
我走进西贝鲁特的哈姆拉(Hamra)区。
不少城市有东西区之分,伦敦最典型,贝鲁特也有此一说。伦敦东西区以阶级划分,东区劳工阶级聚居,西区则是高级住宅区的代名词。贝鲁特有所不同,东西区以信仰分别。东区居民主要为基督徒,西区是穆斯林。
基督教宗派在黎巴嫩一应俱全:东正教天主教新教。其中以一支小小宗派马龙派最为活跃。法国成为当地基督徒的保护者后,马龙派与它建立了密切关系。当年正是在马龙派努力倡议下,托管主法国政府将黎巴嫩山、贝卡谷地,阿卡及沿海几个城市划归为大黎巴嫩。年黎巴嫩独立,共和国正式成立。
穆斯林分逊尼派和什叶派。逊尼派多属中产阶级,接受西方影响,开明而富有。什叶派主要为来自南部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下层民众,他们人口不断壮大,对于黎巴嫩政治生态影响日增。
清真寺
哈姆拉区兼有繁华的商业街和幽静的住宅小区。徘徊在它们之间,我寻找黎巴嫩诗人卡里尔·哈威(KhalilHawi)的寓所。东西贝鲁特面貌有所不同,印象里,东部街道坦直宽敞,多花园围绕的住宅;西部则呈山城式的高下曲折,在现代都市风貌里,仍蕴涵一丝阿拉伯古老街区的迷宫意味。密集的公寓楼群,阳台层层盆栽葱茏,哪里是诗人曾经凭栏处?车流涌过马路,好似河水淌过峻峭狭窄的山谷。出租车驶过身边,不断按响喇叭。这可算是贝鲁特游历中最煞风景的一件事了:满街出租车,风尘仆仆的、独眼车灯的、锈痕满身的,乃至挡风玻璃上横着裂痕的,经过模样似外国游客者身边,必按喇叭示意:“嘟嘟!坐车吧?”有一回我站住看街景,其间有三辆出租车靠拢来盛情邀请,还有一辆在对面路边停下,坚信我将过街上他的车。如此一路走去一路“嘟嘟”,让人不胜其烦,寻史的思绪频频打断了重拾,终究没个结果,只能自我安慰:我所走着的路,哈威当年必定常常经过,街旁的小餐馆洗衣房理发店,应该都有过诗人的踪迹吧?
哈威出身于黎巴嫩山中穷苦的东正教家庭,早年做过砖瓦匠。他热爱诗歌而且才华横溢,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,成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授。他挚爱黎巴嫩这片土地,五十年代的纳赛尔主义又激起他对于阿拉伯民族大团结前景的憧憬。激情来时他写下一首诗《桥》:
拥有同代人的孩子我心已足
从他们的爱我领取我的圣餐。
……
早晨他们过桥无忧无虑年少轻狂
我的肋骨为他们筑成一道桥梁
从东方的洞穴,东方的沼泽
通往新的东方。
我的肋骨为他们筑成坚固的桥梁。
“他们将走过而你将依旧
一无所有,十字架上,独憔悴,
雪夜复雪夜,地平线是炉火灰烬
面包是尘;
你将依旧眼含冻泪悄度不眠夜;
晨光降临邮件送达:
报纸……多少次你反复咀嚼它的内容,
细读。……再读!
他们将走过而你将依旧
一无所有,十字架上,独憔悴。……”转译自伊莎·宝拉塔(IssaBoulatta)的英文译本,见服阿德·阿加米(FouadAjami)著《阿拉伯民族的梦幻之宫:一代人的精神历程》。此诗有不同版本。
诗篇从阿拉伯文到英文再到中文,一再翻译中必有意义失落,但诗人的热忱依然饱满。脍炙人口的诗,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,至今仍是经典。只是,随着纳赛尔主义的失败,以色列复国的冲击和海湾石油的开采,阿拉伯团结成为明日黄花。诗人的无私奉献已不合时宜,人们掉头不顾他以生命筑就的桥,不是“走过”而是“走开”了,惟留诗人独憔悴。年6月6日,以军再度入侵黎巴嫩,挥师北上直指贝鲁特,阿拉伯世界一片缄默。当天深夜,哈威在西区寓所阳台上用猎枪自杀。内战已七年的贝鲁特城中,那一夜诗人自杀的枪声,是纤弱的孤鸣,连邻居都不曾惊动。
中文资料似乎未多提及的哈威,其心路历程其实可以打动许多中国人。诗人生前曾慷慨道:“有朝一日阿拉伯人团结了,告诉我!阿拉伯团结实现之时,如我已死,请派人到我墓旁告诉我!”服阿德·阿加米著《阿拉伯民族的梦幻之宫:一代人的精神历程》,纽约,万神殿书屋年版。这让中国读者想到南宋陆游的《示儿》诗:
死去原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
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毋忘告乃翁。
种族不同时代不同,执着一样失望是否也一样?陆游身后,南宋王师未能北定中原,北方铁骑反倒直下江南,席卷中国。而哈威去世二十多年来,极端主义的兴起,使阿拉伯团结面临更为云谲波诡的困难局面。
我也造访了毗连哈姆拉区、哈威曾求学和教书的贝鲁特美国大学。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创建的这所学校,如今仍是阿拉伯地区的顶尖大学之一,似乎也是贝鲁特的一处著名景点。酒店接待员、出租车司机,抑或偶然邂逅的人们,都会热心推荐,在这个除了鸽岩似乎无多风景可看的城市里,“去看看AUB吧”!西洋风的教学楼,花木扶疏,掩映着地中海的碧波。西贝鲁特在内战中遭受轰炸无数,但无论马龙派民兵还是以色列军队,并不敢动这所负有盛名的学府。同世界上所有大学一样,它的校园里充满年轻人的笑语。阿拉伯民族棕褐色的大眼睛,眼神清澈如黎巴嫩山中洁净的井泉,不见一丝战争苦难的痕迹。想拦住他们问一声:“记得卡里尔·哈威吗?”但终于没问。昨日之日弃我去者不可留,何必为已成历史的一位诗人感伤?
未完待续贝鲁特的景点鸽子岩
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间医院最权威焦性没食子酸法| |